《西北视察记》是一个记者写的通讯集,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在当时的《申报》上进行连载。当时进入新疆采访的记者不多,而陈赓雅以《申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,足迹遍布整个华北、西北,历时一年零两个月,在新疆的终点就是哈密。
书中陈赓雅全面介绍了当时新疆的军事、经济和政治,特别是甘肃的马仲英部队为了地盘和一己之私,对新疆的荼毒和蹂躏,所造成的民族间的仇杀,令人不忍卒读。穷八站本身就穷,经此战火,不但更穷,而且特别苦。
穷十八站与穷八站


在许多书中,穷十八站富十八站有多种说法,一般指的是,走南线,哈密到乌鲁木齐为苦八站;如果走北线,从巴里坤到木垒河为穷八站,从木垒河到从到乌鲁木齐为富八站。
而在本书中,却另有一种说法:从兰州到肃州(酒泉)为富十八站,从肃州到哈密为穷十八站,从哈密到乌鲁木齐为不穷不富十八站。
几种说法,起点不同,但无论哪种说法,哈密的东西两方面均为又穷又苦的驿站这个事实,是推不掉的。有强烈的穷、苦对比,也许更显现出哈密绿洲的美丽和富饶。
穷十八站上的邮差

在1900年前后的游记中,穷十八站虽穷,但每个驿站,尚有客栈两三家,老板大多是入疆退伍的老兵。虽然客栈破败不堪,但毕竟尚可住人,骆驼、马也能吃上草料。经过1931年、1933年马仲英部队的烧杀抢掠,客栈全毁,只剩下残垣破壁。
就在这残缺不全的房屋中,却仍然坚守着一种人,那就是甘新道上的邮差。在作者陈赓雅看来,这里的邮差孤苦可怜,苦不堪言。在沙泉井这个还算比较大的驿站,他写道:“沙泉井原为大站,店屋均已全毁,仅住邮差二人,生活颇形困苦……自星星峡以西,各站邮差,月得新疆银票三百两,用买骑驴所需之铁掌,即去其半,所余百五十两,以四百两合银一元折算,只合三角七分五厘。日掘锁阳,用以果腹。有时哈密当局酌贴白面数斤,熬清受淡,靡言可喻。是知新疆年来邮路,难如内地畅达者,殆非全受地方政治之影响,而邮务本身收入短少,不敷开支,遂致影响工作,实为一大原因。”
当时穷十八站上唯一的留守人员,住的是残缺不全的房屋,吃的是挖来的野果,还不说七百里不见一树的恶劣环境。他们能坚守下来,作者都认为不可思议。
穷十八站沿途倒毙的骆驼与马
穷十八站上的邮差,穷的已经挖野果吃了,经行的商旅,负重的骆驼和马,境况自然更惨。
从疙瘩井往西,一百八十里的路途中,经过苦水井、腰店子、格子烟墩等站。“沿途死马、死驼,不绝于目,尤其腰店子一段,平均每间四电杆,即倒一驼、马。有谓安哈千里途间,平均每三里即死一驼或马,共计之,当多至三百四五十头,穷站之穷,已可想象。”
作者感叹,如果沿途各站有人开店,草料俱全,而驼夫、车主就不会虐待牲畜拼命赶路,驼、马之死,就不会这么多了这么惨了。
如今的几百公里,火车、汽车几个小时飞驶而过,十八站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,唯在历史的烟尘中,使人感叹穷十八站之穷,之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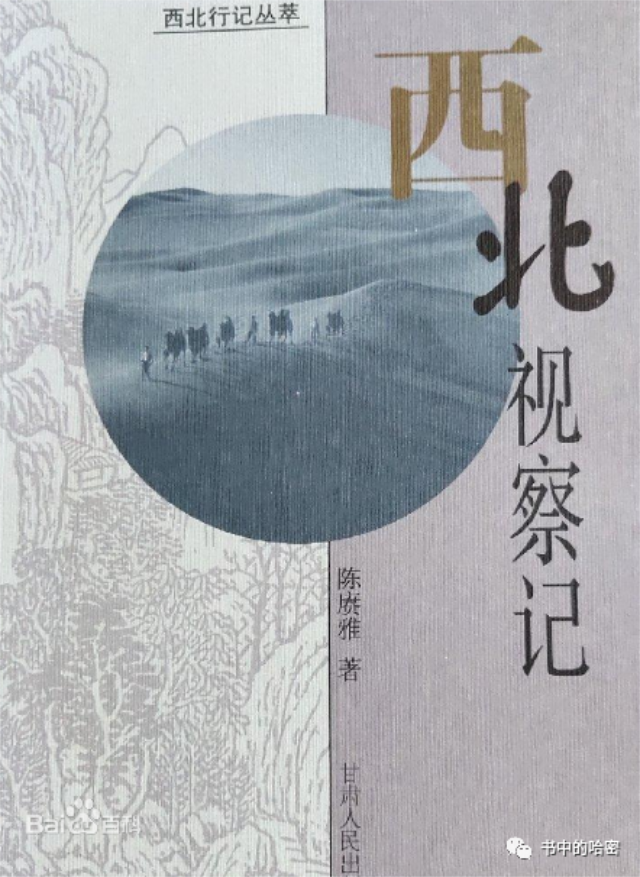
《西北视察记》陈赓雅/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



